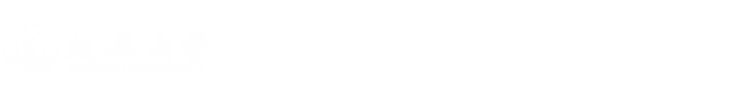一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儒墨同显,一致百虑,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墨子先学儒,后觉察儒学缺点,自创墨学,非儒反儒,补充改造儒学,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重要原理。墨子肯定孔学有“当而不可易”(正确而不能改变)的真理成分。墨家是先秦唯一堪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
孟子推崇墨子兼爱的人格精神魅力。《孟子·尽心上》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提倡全人类兼爱交利,即使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只要对天下有利,都甘愿付出,这种损己利人、大公无私的精神,突显了墨子追求真善美理想的高贵品格。孟子对墨子精神的赞扬,影响深远。
西晋鲁胜《墨辩注序》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孟子非墨辟墨,但其思维表达方式,承自墨子,酷似墨子,辩论模仿墨子惯用的归谬反驳法。《孟子·告子上》说:“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不知类”是墨子应用归谬反驳法的标志词、惯用语,曾用来说服鲁班与楚王,止楚攻宋,孟子出色地加以传承发扬。《孟子·梁惠王上》说:“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孟子归谬辩辞,比喻生动,脍炙人口,众所周知,是世人普遍效法的思维表达范例。
儒墨之学,各有所长,舍短取长,有助于把握全面真理和治国良方,是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思想家对儒墨学关系的标准定性,是今日认知判断儒墨关系的正确指引。
二
从公元前五世纪墨子推出《兼爱》等重要论文,到前三世纪后期墨家《墨经》六篇,历时近三百年的学理积淀,墨家学人从十多个角度,阐发兼爱学说的深层意蕴。墨家“兼爱”论题的论证,强调全人类的共同本性和爱的整体性、普遍性、彻底性、穷尽性、交互性、平等性与不可分割性,强调兼爱是人类善良的理想愿望和奋斗目标。
墨家“兼爱”,又称尽爱、俱爱、周爱,强调不分民族、阶级、阶层、等级、亲疏、住地、人己、主仆、时代等所有差别,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人,都包含在“兼爱”的范围。
墨子“兼爱”讲“仁义”。《兼爱下》说:“兼(爱)即仁矣,义矣。”《墨子》讲“仁”116次。“仁”指爱人,仁爱指所有人相互亲爱。墨子“兼爱”论题的理论基础,是全人类的共同人性论。墨家肯定全人类必然具有共同的本性。《辞过》说:“凡回(运转)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墨子主张“爱无差等”(兼爱),反映手工业行会成员间平等互助的朴素愿望,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的人性论、人格论和人权论。墨家“兼爱”学说,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
墨子“兼爱”论题的命题含义,是“所有人应该爱所有人”,属“应然”的道义逻辑,是“道德义务”范畴,不属“实然”的真值逻辑(真势逻辑和事实逻辑)范畴。《墨经》列专条举例证明,画龙点睛,一语道破“道义与真值”两种不同逻辑的本质区别。
《墨经》用论据“有人不黑”,反驳论题“所有人黑”,推论有效(宜)。因论据、论题都关乎事实,合乎真值逻辑同一律的规则。用论据“有人不被爱”(如盗贼、攻国者),反驳论题“所有人应该爱所有人”(兼爱),推论无效(不宜)。因论据关乎事实,属“实然”的真值逻辑范畴,论题关乎理想,属“应然”的道义逻辑范畴,不属“实然”的真值逻辑范畴。逻辑系统不同,推论形式规则相异。
三
秦汉学界,儒墨对举,孔墨并提;汉后至清,墨学衰竭。
作为墨子“兼爱”理想深刻理论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人性论,不符合宗法等级制的要求。“兼爱”理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超越性善良愿望和理论假设。
儒家“爱有差等”,适应宗法等级制要求,随血缘亲疏远近,施爱厚薄不同,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亲亲尊尊”的“血统论”,是“中世纪”漫长宗法等级制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墨子坚决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主张“可学而能”的共同人性论,是科学的认知理论(认识论),认为知识由后天学习得来。《尚贤下》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只凭血统高贵,治理国家,不通过学习,获得智能,“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就像叫哑巴当外交官,聋人当乐队指挥,必然越治越乱。
孟子辟墨,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辟”即驱除、屏除、排除。宋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说:“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孟子辟墨,孔孟之道才能鲜亮发光。
《兼爱上》说:“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墨子明说“爱父爱君”,从未提倡“无父无君”。孟子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率兽食人”,罔顾事实,不讲道理。
孟子的攻击,演变为“中世纪”两千年封建官方打压墨学的“霹雳”,汇聚为墨学中绝的强势外因。《四库全书》收入儒者著作,有二十四卷二十五处,长篇大论,恣意发挥,无限上纲,诬蔑“墨氏兼爱”,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认为洪水猛兽之害,见于一时,墨学兼爱之害,起于无形,遗祸永远。汉至清两千多年,封建国家机器汇聚辟墨洪流。
孟子攻击墨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视为对墨子的政治结论和人格定性定位,绝无翻案平反的一丝可能条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儒学界把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真理标准,是典型“以权威为据”和“以众取证”的谬误,充斥心理相关型和论据空缺型的诡辩。
在极端恶劣的政治语言环境下,若有人为墨子说一丝公道话,与儒家传统议论些微不合,即刻被株连定性为“异端邪说”,猛遭围剿挞伐。
清汪中(1745—1794)幼年孤贫好学,1780年35岁得“生员”(秀才)头衔,为“选拔贡生”。汪中搜集墨子论述,作《墨子序》,推崇墨学,说墨子是救世“仁人”,批评孟子诬枉墨子“无父”。汪中在《墨子序》中说:“彼(指墨子)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其以耳食,无足怪也。”墨子兼爱,是教育天下作儿子的孝顺父亲,孟子说墨子兼爱为“无父”,显然是冤枉墨子。“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孔、墨、孟三子,因道不同不相为谋,纯属正常。汪中这两句合乎人情事理、并无不妥的话,竟引来官方儒者翁方纲罗织罪名,猛烈攻击。
翁方纲是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鸿胪寺卿,文渊阁校理,司经局洗马,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四库全书》八处提到翁方纲。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五说:“有生员(秀才)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方授楚说:“当时所谓‘名教之罪人’,重则足以砍头杀身,以此归罪汪中,足见其形势之严重。”
在当今不同文明互补互鉴的全新时代,辨识墨子兼爱学说的精义,记取孟子不当辟墨的历史教训,探寻墨学中绝的动因,推进儒墨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历史赋予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儒墨学界应携起手来,努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儒学研究和墨学研究交流合作,开辟儒墨学兼容创新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