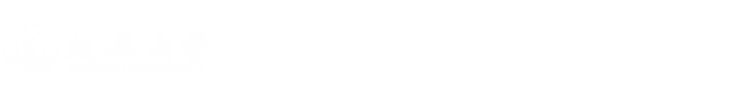延安时期,县级干部的职责范畴可谓巨细靡遗,其工作生活之艰辛亦是难以想象的。县级干部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和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倘若没有崇高的精神信仰,丛集于一身的工作任务实在难以很好开展。其精神信念究竟从何而来?只要关注当年中外人士在延安的观察感受,即不难发现其中的缘由。
“共产党对干部的教育十分重视”。
一位国统区人士到访延安后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共产党对干部的教育十分重视。”在全部教育工作中,干部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
这位国统区人士的“发现”是精准的。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讲话中就曾指出:边区的县级干部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要提高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办事能力。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
1938年12月,《新中华报》发出了“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号召。边区民政厅要求在职干部必须每天抽出2小时学习。在甘泉县,规定县级干部一律要参加干部学习组织,保证每天2小时的学习时间,各单位必须统一执行。学习热潮随即开启,精神信念由此筑牢。
“到乡上去照,才能照见那里还有些灰尘,才能赶快把它洗掉,也只有到乡上去挖,才能发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马上解决它”。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延安访问之后曾说:“县长概是民选,正式集大多数民众公举,非同有名乏实私弊。”
革命时期通过直接选举的形式任用县长,其中内含的逻辑是县长由民众直接选举,自然应该为民众负责。换言之,在县长的思想理念中,群众就是他们的精神信仰。故而凡在一些县区内得不到群众热忱拥护与反映的,政府就要立即考虑自己工作中是否发生错误与缺点。如果群众对政府产生冷淡情绪,就要立刻想到政府的领导方面存在哪些错误与缺点,或者是政府内有不为群众所信任的人存在,或者是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或者是政府对群众没有说服精神,而采取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架子。
其时,县长的施政效果如何,最终也要在乡村“照镜子”。按照党外人士李鼎铭的说法,只有“到乡上去照,才能照见那里还有些灰尘,才能赶快把它洗掉,也只有到乡上去挖,才能发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马上解决它。这样,下情了解了,领导的正确性了解了,工作检查了,问题就解决了,并且由此取得了经验,作为领导和推动全局的根据。”这种办法在李鼎铭看来,确是“医治今天我们政府领导人员的毛病的良方”。
“农民出身的县长主要还是处理农民的事,这样比较亲切”。
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到访延安后的感受是“农民出身的县长主要还是处理农民的事,这样比较亲切”。
事实正如这位记者所言,陕甘宁边区的县长几乎全是当地农民出身。因为只有本地干部大批成长并且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党才能在根据地生根。
县长由本地人担任,无论是语言习惯还是生活方式,都有着共同一致的习惯特点。同时本地干部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
对于民众而言,在选举县长时,因被选举人是本地人,选谁不选谁心里是比较清楚的。故而最终被选举的县长,自然在民众心目中有着相当的威望。也正是由于如此,民众对选举县长非常认真,只要召开选举会,民众都会敲锣打鼓庆祝游行。延长县在召开选举会议时,群众不仅热烈庆祝,还特地向大会送酒食,以体现民众对选举的关切。
“‘官长’这一类的名词被人嘲笑,没有表示阶级的徽章,也没有头衔”。
一位西方记者对延安产生了这样的观感:“‘官长’这一类的名词被人嘲笑,没有表示阶级的徽章,也没有头衔。每个人,连非共产党员在内,都被叫作‘同志’。但是表示责任位置的等级,在工作上严格的保持着。”正如这位西方记者所说,革命时期干部的精神世界中,诸如“官”这样的概念,是一个极其刺眼的概念。
1938年4月初,薄一波和牺盟会干部谈话,要求派人到沁县担任抗日县长,牺盟会的党员特派员都不愿意担任此职,“他们认为县长是官,而好人不当官”。牺盟会特派员史怀璧开始也不愿意去。薄一波随即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旧社会当县长认为是光宗耀祖的事。现在共产党员当县长是革命的需要,是为党的事业去当县长。随后史怀璧才带着薄一波送给他的一匹日本大洋马、一支手枪走马上任了。
《星洲日报》的一位华侨女记者到山西五寨县政府访问吕尊周县长,去后发现县政府非但没有以往衙门中“森严可怕的气氛”,而且在县长办公室内,她发现除了办公桌、椅、两张长板凳和一个书架之外,其他摆设一无所有。这位记者同他谈话时,发现“吕县长没有官老爷的臭架子”,与其交流甚至“感觉到同自己父亲谈话一般的自然亲切”。
毫无疑问,延安时期县级干部的精神信仰,归根结底是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砥砺而成的。革命时期地方干部的精神信仰在革命的发展成长壮大中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容低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党领导革命的胜利,又何尝不是缘于这些地方干部的胜利呢!